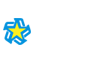舞會進入高潮已經(jīng)兩個小時了海納·布里澤嘆了口氣。選擇這個地方過生日他倒是很高興。但當他吹滅了三十五支蠟燭、打開了禮物以后,客人們卻要自己掏錢支付這次生日舞會。
他的夫人是這次舞會的組織者,此時也悶悶不樂起來。
毫不奇怪,一杯接一杯地喝,最后都把大家給喝垮了,而且地毯上到處都是煙蒂。
電話響了。這么晚了還有人祝賀?海納拿著電話機走進化妝室,用一個手指堵住了左耳朵,右耳朵傳來了一位老相識的聲音:“晚上好,海納!對不起,這么晚了還給你打電話。這是什么聲音啊?你開了迪斯科舞會嗎?”
“只是小范圍慶祝一下,你知道……”
“沒邀請我?那好吧,我說得簡短些。格雷克·呂特爾福特要退休了,他想物色一個合適的人選接管他在倫敦的畫廊。我使他堅信,只有你合適!他愿意給你出個朋友價。如果賣掉你在依策荷的財產(chǎn),你就會夢想成真了!”
海納激動地返回客廳,點著新煙斗以使自己平靜下來。
煙斗也是他太太送的禮物,她同時還送給他幾方黃色絲綢手帕,上面交織繡著他姓名的起首字母。一方手帕他已經(jīng)插在了上衣的翻領里。他抽著煙斗,噴著濃煙,掃視著來賓。他
的合作伙伴路德維希·拉梅爾穿著一件厚毛衣,蜷縮在沙發(fā)的一角里。還好,他太太安內(nèi)利沒來,她去親戚家度周末了,海納討厭她。
大學畢業(yè)后,海納和路德維希把所有的積蓄都攢到了一起,兩人在依策荷開了一家藝術畫廊。對一個省來說,他們的畫廊運作得相當不錯,但同格雷克·呂特爾福特在倫敦的畫廊相比真可謂小巫見大巫了。那些真正的大畫家和有名的雕塑家都在那兒展出他們的作品。那兒的氣氛適合海納!他今天可是交了好運了!可是賣掉畫廊必須首先爭得路德維希·拉梅爾的同意。他很有可能壞了他的好事。
凌晨三點鐘,海納終于可以給最后一批客人叫出租車了,也包括路德維希,他喝了幾瓶葡萄酒后坐在沙發(fā)上睡著了。
“哎呀,我這把老骨頭,渾身都疼。”他痛苦地喊叫著,“太好了,馬上就要到明天了。”路德維希的風濕病和他的懶惰以及他一直戴在脖子上的小點子花紋領結一樣,構成了他的個性。海納把他拉到了一邊兒。
“你明天還能到畫廊來一趟嗎?”他問道,“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談。”路德維希正在腰部做著二指禪功按摩術,這時他吃驚地停了下來,說:“可以,如果你這么說,但不能太早,也許十八點吧。”
第二天晚上,海納把車停在了畫廊前,他透過明亮的辦公室窗戶,發(fā)現(xiàn)路德維希已經(jīng)到了,他悄無聲息地進了大樓。
燈突然滅了,路德維希嚇了一大跳,接著,他又聽見走廊里傳來了腳步聲。報警裝置沒有電可就不起作用了!他迅速跑到房間的一個角落,那里至少還有點亮光:大衣柜的后面有個保險絲盒。
“喂,路德維希!我也正要查看一下保險呢。我剛才試了一下一號大廳的照明設備。得馬上讓電工過來看看。”
“哦,天哪,海納!嚇死我了!
借著手電筒的光束,海納注視著路德維希恐懼的目光。
路德維希不能容忍別人把他看成一個可憐的、無足輕重的人。但如果海納想在倫敦有所突破,他很可能會拖累他。他盡力控制著自己,對路德維希講了格雷克·呂特爾福特的提議。
“海納,我不理解你。”路德維希嘆息說,“我們在這兒挺好的,去倫敦干嗎呢?”
“你真的不明白嗎?這對于我們來說是個絕好的機會!在倫敦我們將是最好的,我們可以大把大把地賺錢。整天乞求當?shù)氐木庉媯?讓他們報導畫展的開幕式,對此我早已沒興趣了。”
“海納,這是你的問題。我在這兒很幸福,我永遠也不離開。我看你想怎么著就怎么著吧。”
“你說什么?我只有把這兒的一切都賣掉,才能擁有呂特爾福特的畫廊。地皮、設備,尤其是花瓶。”海納指的是這里收藏的一批中國瓷器,那是依策荷的一位收藏家的遺贈。一只特別漂亮的花瓶就擺在辦公室里。”
“絕不,海納,絕不。”
“你可真是你媽媽的寶貝兒子,一個發(fā)胖的、患有風濕病的寶貝兒子!我希望,你不久就葬身在你那些可愛的農(nóng)民畫里。”
路德維希站起身,拿上大衣走了。海納兩大步就追上他,憤怒地拽著他的頭往門框上撞去。路德維希呻吟著倒了下去。
海納感覺手上有粘粘的液體:血,路德維希的血。他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擦著血,路德維希又嘆了一口氣,嚇得他把手帕也掉在了地上。然后,他跑進廚房喝了一杯水,又返回了辦公室。他極力控制著自己。他驚奇地看到,路德維希爬到了窗子附近,蜷縮在加熱器旁。海納屏住呼吸,架著路德維希的胳膊,生拖硬拉地穿過走廊把他拖到了地下室樓梯旁。他把重重的軀體扔進地下室后,自己緊跟著也跑了下去。他摸了摸路德維希的脈搏,他死了,終于死了。海納又回到辦公室,除去了所有的疑跡。
他又一次合上了一號大廳的保險—“啪”一聲,保險又壞了。
第二天,海納一跨進辦公室便看見亞當斯夫人坐在高背椅上,臉色慘白,她和每天一樣來打掃衛(wèi)生,發(fā)現(xiàn)了路德維希的尸體。“布里澤先生,您來了真是太好了,”她抽泣著,“真是太可怕了。”海納握住她的手,“可憐的亞當斯夫人,您安靜一下。”
她睜大了眼睛,目光越過海納朝門口望去,他轉過身,有人抬來了一口黑色棺材。一位刑警拍著他的肩膀:“布里澤先生嗎?我們還要問您一些口供。”
“還有不清楚的地方嗎?”
“其實沒什么。一切跡象表明,保險壞了以后拉梅爾先生在黑暗中被絆了一下,然后順著地下室的樓梯跌了下去。
“您最后一次見到他是什么時候?”
“星期六晚上,在我的生日宴會上。
一聲尖叫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但你最大的生日愿望今天才得以實現(xiàn)。”路德維希的夫人走了進來,身后跟著警長。
“你在那兒胡說什么呀,安納利。”海納驚得目瞪口呆。
“路德維希不幸遇難了。”
警長插話說:“不過還有幾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在他的頭上發(fā)現(xiàn)了幾塊木屑,從樓梯滾下來是不可能有木屑的。”
“他肯定是在黑暗中把頭給撞了。”海納認為。
“你只管去想像好了。但殺害路德維希的兇手會說出事實真相的!”
“你說兇手?你聽說什么了?”海納六神無主地看著警長,“您也許懷疑……”
安納利打斷他的話:“路德維希不是一直妨礙你嗎,你想最終成為畫廊的獨裁者,想當一個大人物,不要自己收賬。這回你殺了他就可以實現(xiàn)自己的夢想了。”
海納氣得火冒三丈。難道這個老妖精真的以為他和她的丈夫一樣嗎,一個小小的畫廊就是他的一切?“你只管瞎編好了。”他喊道,“要不要我給你看一看,畫廊對我有多重要?”
海納舉起那只貴重的中國瓷瓶,高高地舉起來,然后憤憤地“啪”的一聲摔在地上。隨著震耳欲聾的一聲響,這件貴重的東西成了碎片。
“這是什么?”探長彎腰看著地上一堆碎片。海納看到他那方浸滿血跡的手帕掉了出來,是那方黃色絲綢手帕,上面交織地繡著他姓名的起首字母;第一次在辦公室試圖謀殺后曾經(jīng)用它擦過手。肯定是當海納急急忙忙去廚房時,路德維希用盡最后一絲力氣把它塞進了花瓶里。
“這只小臭蟲!”海納伸了個懶腰。現(xiàn)在他真想把路德維希再干掉一次。